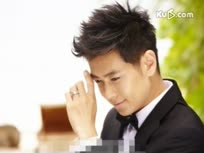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8月2日就原告美國禮來公司(Eli Lilly and Company)、禮來(中國)研發有限公司與被告黃某間侵害技術秘密糾紛案件發出行為保全裁定,裁定禁止黃某披露、使用或允許他人使用上述兩公司主張作為商業秘密保護的21個文件內容。
《法制日報》記者了解到,這是新民事訴訟法實施以來,我國首個依行為保全規定作出的商業秘密行為禁令。
被告下載保密文件拒不刪除
原告訴稱,2012年5月3日,研發公司與黃某簽訂勞動合同書,聘用黃某從事化學主任研究員工作,合同期為2012年5月3日至2015年5月2日。雙方保密協議約定,黃某在受雇期間獲得的原告的保密及專有信息,與原告的銷售策略和市場策略有關的保密及專有信息,黃某負有保密義務並不得向任何其他個人或組織泄露。
2013年1月19日,黃某未經同意私自從原告的服務器上下載了公司的保密文件,事后拒不刪除。2月1日,研發公司向黃某發出停職通知書。當日,黃某提交辭職信。此后,研發公司數次派員聯系黃某,要求其配合刪除涉案的機密商業文件,但黃某拒絕配合。同月27日,研發公司發出勞動關系終止通知函,通知於當日立刻終止與黃某的勞動關系。
原告認為,黃某違背公司規章制度及保密協議內容,侵犯原告商業秘密,使原告商業秘密處於隨時可能被二次外泄的危險境地,故訴請判令黃某立即停止侵犯原告商業秘密行為,賠償原告損失及原告為制止侵權行為支付的律師費、公証費、調查費、翻譯費及其他合理費用共計2000萬元。
同時,原告向法院遞交了“請求責令黃某對已從原告處盜取的21個商業秘密不得復制、披露、使用或者允許他人使用”的保全申請,並提供擔保金10萬元。
上海一中院審查后認為,原告的申請符合法律規定,作出如上裁定。
新民訴法提供禁令依據
上海一中院民五庭庭長劉軍華介紹,我國專利法、商標法、著作權法,均已設立專門的禁令制度,即權利人或者利害關系人有証據証明他人正在實施或者即將實施侵權行為,如不及時制止,將會使其合法權益受到難以彌補的損害的,可以在起訴前向人民法院申請採取責令停止有關行為的措施。
“而同樣作為一種知識產權的商業秘密,在當前司法實踐中,卻缺少專門禁令制度的保護。”劉軍華表示,作為很多公司企業核心競爭力的商業秘密,一旦泄露將會引發嚴重后果,輕則使公司企業投入的研發成本或累積的競爭優勢付之東流,重則造成無法挽回的經濟損失,甚至帶來毀滅性打擊。
新民訴法第100條增設行為保全制度,人民法院對於可能因當事人一方的行為或者其他原因,使判決難以執行或者造成當事人其他損害的案件,根據對方當事人的申請,可以裁定對其財產進行保全、責令其作出一定行為或者禁止其作出一定行為﹔當事人沒有提出申請的,人民法院在必要時也可以裁定採取保全措施。
“這一規定為商業秘密糾紛中採取禁令措施提供了法律依據。”劉軍華對記者說,一中院的裁定,就是依據行為保全規定,首次在商業秘密案件中採取的行為禁令措施。這一禁令有利於防止申請人因商業秘密的公開而遭受難以彌補的損害,是加強知識產權司法保護的有力措施。
裁定具有重要示范意義
“新民訴法生效前,針對涉嫌侵犯商業秘密的行為從未頒發過訴前禁令。”華東政法大學知識產權學院副院長、教授黃武雙接受採訪時表示,原因在於,調整與商業秘密獲取、披露、使用等有關行為最高位階的反不正當競爭法、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不正當競爭民事案件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等實體法律規范,以及修改之前的民訴法,均未規定可以針對侵犯商業秘密的行為頒發訴前禁令。然而,專利法第66條、商標法第57條、著作權法第50條均規定,可以針對侵犯專利權、商標權和著作權的行為頒發訴前禁令。
黃武雙介紹說,新民訴法生效之前,是否可以針對侵犯商業秘密的行為頒發禁令,一直是實務界和學術界關注的話題。上海一中院的這項民事裁定,支持了原告禮來公司的訴前禁令措施,將成為侵犯商業秘密行為訴前禁令的范例。
同時,法院在裁定能否針對侵犯商業秘密的某個具體行為適用訴前禁令時,需要審查是否存在使權利人合法權益遭受難以彌補的損害、權利人勝訴的可能性、禁令是否危及公共利益等因素。
黃武雙表示,上海一中院裁定禁止被申請人黃某披露、使用或允許他人使用申請人美國禮來公司、研發有限公司主張作為商業秘密保護的21個文件,所保護的商業秘密及其載體明確、具體,具有極強的司法操作性。
“美國、德國等發達國家的權利人,針對侵犯商業秘密行為申請訴前禁令的情況較為普遍,法院在審查平衡權利人和涉嫌侵權人利益諸要素后,支持訴前禁令的實例很多。”黃武雙對記者說,近年來,來自外國企業、政府機構和律師事務所的某些人士一直對我國的商業秘密保護水准有所詬病。新民訴法填平了商業秘密保護的低窪之處,上海一中院的裁定具有重要的裡程碑意義。(記者 劉建 通訊員 潘靜波)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間
分享到QQ空間
 恭喜你,發表成功!
恭喜你,發表成功!

 !
!